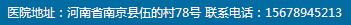玉字新考赵毅颖
内容提要:许慎《说文解字》对“玉”字像三块玉相连的解说沿袭至今,但这并不是“玉”字象形的本源。从构形起源上破解“玉”字象形所本依形象,才能正确分析“玉”字及其衍生字的衍变过程和文化内涵。关键词:人面;构形起源;原字;衍生字;转义《说文解字》:“玉,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古文作‘玉’。”[1]许慎对“玉”字的解释是:像三块玉相连。沿袭至今的这个解释若是对三横一竖的篆书“玉”字,从字面形态上解释似乎还说得通;但要解释《说文》中提到的古文“玉”字,即带有对称两点的“玉”字(图1、《金石字典》、中国书店、年4月第一版),是说不通的。
图1
“玉”字构形起源及其衍生字形成的原字链的研究,于汉字文化乃至华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一、“玉”源人面这是一方5公分宽的陶质“印章”(赵毅颖年2月收藏)。陶印看似脸谱,双钩线条刻画眉眼口鼻,形象而简练,见图2。
图2
印面刻画的是符号、文字、图腾?将此陶印刻画眉、眼、口及鼻翼、脸颊分界的双钩线条以外填墨,竟是个古文“玉”字形,见图3。
图3古文“玉”字的第一横在这个陶印里相当于额头位置,第二横是眉下眼睑位置,第三横是下颌部分,两点为脸颊部分,一竖即是鼻子。古文“玉”字与陶印双钩线条的阴阳相印是巧合?《金石字典》里有一个古陶“玉”字,是有对称两“点”的,见图4。图4
古文“玉”字出现之时,汉字发展已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先民已具有从图画提炼“字划”的自觉意识和能力。将陶“印”的五官刻画提炼成字,如同印章的阴阳文转换,刻画眉、眼、口、鼻翼脸颊分界双钩视为阳文,余处同古文“玉”字形的空白为阴文。对比阴文、阳文,阳繁阴简;阳文框内左右两部分对称断开,结点繁多;阴文则第一二笔贯通即成,两面对称之眼部、鼻翼脸颊分界部分转笔,以两点代之,显然简省,见图5。
图5
商代甲骨卜辞及甲骨文图书资料没有这个古文“玉”字。理论上讲,早期甲骨文应该有古文“玉”字,物证其真实存在是“玉”字考证的关键。古文“玉”字肩胛骨刻(赵毅颖年5月收藏,据流通者说,出自松花江哈尔滨段。),高43公分,上宽部残损,存40余字,一个标准的古文“玉”字居中镌刻,见图6。目前,这应该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古文“玉”字文物。
图6
另一件,嘴形“玉”字肩胛骨刻,高51公分,60余字,有四个古“玉”字,其中两个下横画向上弯曲,两个刻画成嘴形,口鼻象形特征更为明显,应是较古文“玉”字更早些的演化形态,进一步证明了“玉源人面”,见图7。
图7
松花江骨刻文为大型古哺乳动物化石,文字字口与骨面风化一致,气韵高古,为早期象形文字;古文“玉”字属甲骨文字典中未录、未见之字,非造假所能为。松花江骨刻文是新石器早期文字,具有重要考古价值,有待加强保护和深入研究。通过对陶印和古文字书迹解读考证得出结论:古文“玉”字是象形字,是由人面五官形象提炼而出。古文“玉”出现在汉字形成初期。汉字形成、发展过程中,“六书”使众多汉字相互关联,尤其是“原字”,与其衍生字的“形”、“义”密切相关。下面分析由原字“玉”变化、衍生的“巫”、“王”、“工”“天”、“大”、“人”字的衍变过程及文化内涵。
二、古文“玉”即是古“巫”字古文“玉”的本义并不是指玉石。新石器早期,王国还没有出现,部落中地位最高者即是巫。巫掌握着当时的“先进文化”,并成为“后世天文、历算、医术、宗教的起源”[2]。巫者在探索世界过程中,以各种材料(木、骨、陶、石、等)作为表现载体。在这个过程中,巫之地位在部落群体中确立。巫者以何形象、象形代表?人面形象理所当然是首选。人面“玉符”(陶印)及古文“玉”形象代表巫,与甲骨文对比,“巫”字就是古“玉”字的变形,两点居中而已,见图8(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年1月第一版)。
图8
巫字的变形主要是为甲骨文的契刻方便,甲骨朱书后以刀刻的方式是,先完成一个方向笔画(横画),再旋转甲骨九十度,刻另一方向笔画(竖画)。轴对称形的“巫”字,不必考虑其方向性,不需分辨如古文“玉”字形的两点与各个笔画之间的空间位置的准确性,旋转后与旋转前笔形、刻法一致,是程序化的操作,较古文“玉”字契刻省时省力。古文“玉”是甲骨文“巫”的原字。古文“玉”即是古“巫”字。诅楚文“巫”字更接近古文“玉”字形,见图9(《金石字典》)。
图9
诅楚文“玉”字两点变化上移至上二横间,可见古文“玉”两点位移变化轨迹,亦是佐证,见图10(《金石字典》)。
图10
“玉”字初始出现时,巫面“玉符”雕刻(其取材无论是木、骨、陶、石)即是巫师“通天”的信物和部落群体崇拜的图腾。巫者被称为“玉”,巫亦自称为“玉”。“玉”是最早的人称称谓字、自指字,为巫、巫神义。据陈梦家考证,巫在殷商为神名[3]。原始部落中,只有有着崇高地位的巫才能称“玉”。“玉”字产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
三、“玉”字与“王”字、“工”字“玉”字演化为“王”字。左右对称带点的古文“玉”字发展至甲骨文、金文,字形发生变化,有两点的“玉”字不见了。罗振玉说玉:“至古金文皆作王,无作玉者。”[4]就是说古文“玉”至商金文作“王”。有两点的“玉”字是如何变成“王”的?为什么古文“玉”字从商甲骨文至今弃之不用?为什么“王”读“玉”?读“玉”的“王”在甲骨文中为什么鲜有应用?读“玉”的“王”是指玉石吗?真正指玉石的“玉”字何时出现?在陶印“玉符”中,“玉”之两点表现脸颊及鼻翼。当用竖画肥笔可以表现鼻、口形状时,表现脸颊及鼻翼的两点是多余而可以简省、简化的,“王”字形由此而来,见图11。
图11
古文“王”第三横上翘即是表现嘴形,见图12(《金石字典》)。
图12
甲骨文的“王”字以双钩表现竖画的肥笔部分,这是为了顺应甲骨文刻制工具,以刀代笔,表现框括,其实质与陶印“王”同形,见图13(《甲骨文字典》、松花江肩胛骨刻文)。
图13
董彦堂认为,没有上横的是早期甲骨文的“王”字[5],见图14(《甲骨文字典》),这只是限于资料的判断,不能以此确定早期甲骨文的字形。松花江骨刻文“王”(图13)有上横,而其年代要比殷商甲骨文早得多。
图14
金文的“王”字是以竖画和下横作肥笔表现口鼻的,见图15(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学林出版社、年5月第一版)。
图15
陶印“玉符”里含有的“王”与古文、甲骨文、金文的“王”字形态一致,这不是巧合。古文“玉”字被肥笔、双钩的“王”表现、简化。王国出现前(最高统治者“王”没有出现前),“王”字读音与古文“玉”是同音一致的。从“玉”字产生到其发展初期的一段时期里,古文“玉”、“王”不分。至于“玉”、“王”二字字义分别,是文字发展过程中之赋意。赋意“王”(读wang)时,巫之地位进一步转化,政教合一、巫王一身,“王”(读wang)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字,“王”成为一字二音、二义。“商王始得称王”对于先王称“王亥、王恒、王矢,后世追尊”[6]。商王始称王,是现存资料可考的年代,而实际时间,还要早得多。具有三横和下半分叉一竖的是甲骨文“王”字“标准字形”,这个字形于“天”字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见图16(《甲骨文字典》“天”字、二期合集)。
图16
近现代古文字学家对“王”字竖画和下横连接形态的象形解释有如下四种[7]:火形,罗振玉、马叙伦、顾实、王国维、朱芳圃、吴大澂;斧形,林沄;人体端坐形,徐中舒;男性生殖器:郭沫若。上面四种说法都是没有充分论据的猜想。“玉”字分离出“工”字。我们以面部刻画的阴阳简图示意,便可明显看出来“工”字的提炼过程,与“玉”字相比,“工”字简化了“眉”,见图17(《甲骨文字典》、《金文大字典》)。
图17
“巫”、“工”二字都是来自于人面“玉符”,《说文》言工“与巫同意”[8],由此可证。“玉”、“巫”、“王”、“工”皆由人面形象象形而来,且皆为称谓字。
四、“玉”字的转义“巫”字从“玉”字分离出来,作为最高统治者之“王”字又从“玉”字赋意分离出来;更因年代久远,历数千年之变,人们已不知古文“玉”字的巫义;新石器时代“巫玉”的繁盛,至殷商,巫早已成为以玉通天的专司,从玉石器文化兴起,巫与玉石、玉器便紧密联系在一起,玉几乎成为巫之代名;本义指巫的“王”(读yu)已被“巫”字取代而弃之不用,成为与玉石、玉器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字。因此,“王”(读yu)字的称谓义消失,退而专指其质材。然而,“玉”字经历了漫长的转义的过程。在专指玉石的“玉”字未转义分离出来之前,对于古文“玉”及甲骨文、金文大篆“王”字等,指为玉石之玉的解说都是错误的。甲骨文字典中的“玉”作“丰”形,见图18(《甲骨文字典》)。最早对这个“丰”释为“玉”字的罗振玉的根据是,甲骨文中找到三个合体字“王”旁作“丰”,并认为“丰”是“王”的一竖露出两端。[9];而郭沫若却说:“金文从玉之字颇多,无一从丰作者。”[10]是不同意“丰”释为“玉”的。孙海波、陈梦家定为“工”字,解义是玉的单位词[11]。甲骨文的这个“丰”释为“玉”字是错误的。
图18
甲骨文、金文中的“王十丰”,“丰”非指玉,首字“王”也不能释为玉,这个“王”应是王权、封权、封赐义。近现代甲骨文字典将这个“丰”误认为玉石的玉字。甲骨文中无玉(指玉石)字。就目前资料看,殷商甲骨文、金文中从“王”旁合体字,无一字与玉石相关。专指玉石的“玉”的转义出现很晚,殷商甲骨文找不到与“王”组合指玉石的词。西周金文出现“环”、“璧”、“璜”字及与“王”组合指玉石的词如“王环”,可作为“王”(读yu)转义时间的考据,见图19(《金文大字典》西周毛公鼎、召伯虎簋、番生簋)。据此,“王”字(读yu)转义在西周。
图19
至于现在应用的一个点的玉字,是为了区分这实在难以分清的多音多义的“王”,这已是在汉代隶书的演化了。
五、“王”字减笔成天”、“大”、“人”字智慧的先民对于人面这样重要的成字形象宝藏及“玉”字的提炼并没有结束,对于汉字及中国文化意义重大的“天”、“大”、“人”是从“玉”字中提炼出来的第二层级“会意”字。“天”字。甲骨文以双钩表现竖画肥笔的“王”字与“天”字比较,只多了下面的一横,将甲骨文的“王”字去掉下面一横就是“天”字。甲骨文“王”竹字下面一横意象地,“天”字的成字内涵是——离地为天;“巫王”有通天法术,以王字演化为“天”字时,合于“巫王”的旨意。从松花江骨刻文已有“天”字看,早在王国出现前,巫有着绝对定位(可称“巫王”)时期,就出现了“天”字,见图20(《甲骨文字典》、松花江大肩胛骨刻文、《金文大字典》)。
图20
甲骨文“天”字第一横有刻为“口”,有第一横上又横,有腰间对称又两笔,皆源于古文“玉”字象形表现。于省吾指出:“天字构形的起源,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后世说文学家和近年来古文字学家对天字的说法,聚讼分歧,甚至在六书归属问题上,也有指示会意形象之不同。令人困惑莫解。说文据已伪的小篆而又割裂一与大为二字,其荒谬自不待言。”[12]千年悬疑可以溯本寻源了。甲骨文的“王”字与“大”字(图21、《甲骨文字典》)比较,少了上下二横。甲骨文“王”字下横意象为地,上横意象为天,构形内涵是——天地之间为大,普天之下王为大,由“王”演“大”,这又合于王的旨意。
图21
甲骨文“大”与“天”同,可见二字同源。“人”字。甲骨文的“王”字与“人”字比较,剩下“一撇一捺”,是甲骨文“王”字的双钩的竖画,在古“玉”字原形象为“鼻子”。甲骨文中“自”字是一个象形的鼻子,这个“人”也同样是“鼻子”,但比“自”更为抽象。“人”字构形内涵是——人立于天地之间,并仍含有指鼻称谓义,见图22(《甲骨文字典》)。
图22
至于甲骨文中“人”字与甲骨文“王”字竖画原形的差异,是顺应刻制工具及书体结构变形;将一长一短两笔交点上移,以求上紧下松,重心平稳,长笔作钝角,求得均衡。《说文》言“天”字,“从一大”[13],许慎只知道六书会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独体字合成,不知古人造字的减笔法。由一个独体字减笔成字为首次发现,“天”、“大”、“人”三字六书归属可称为“减笔会意”。古文“玉”到“巫”、“王”、“工”的演化属于同源人面的象形演化,为第一层级;第二层级“天”、“大”、“人”的衍化是由甲骨文“王”字“减笔会意”,进入到抽象会意,是汉字发展历史中的“高级阶段”;第三层级是更为众多的合体形声、会意等六书成字。由“人面”及古文“玉”字生成的原字链为汉字成字源流的重要一支。注释:[1]、[8]、[13],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年12月第一版、10页、页、7页;[2],《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年第一版、页;[3]、[4]、[5]、[6]、[7]、[9]、[10]、[11]、[12],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年5月第一版、页、页、页12行、页、——页、页、页、页、页。
声明:本文为原创作品,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赵毅颖,沈阳人,年出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史前文明研究者,现任地区机关报副刊编辑。
如果喜欢我们的文章,可以长按下面的指纹部位,文案策划总监北京那个医院治疗白癜风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