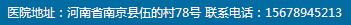当前位置:鼻肥 > 鼻肥大医院 > 尚武美女们爱穿的长筒靴原来是暴力哥们的野 >
尚武美女们爱穿的长筒靴原来是暴力哥们的野
《步辇图》局部,着长靴的吐蕃使者朝见唐太宗,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是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文
朱世巍
《国家人文历史》年11月上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何东西一牵扯到起源什么的,就变得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甚至关系到民族国家的面子荣誉等等而大打口水仗。长筒靴似乎是个例外,没什么人热衷于争夺它的发明权。一般认为这玩艺最初的雏形大概是绑腿(或者胫甲什么的)与鞋身的结合体,大概在年前形成为一个整体。这一时间的依据是新疆楼兰出土的一双羊皮女靴,而它的发现地点似乎又证明其创造者或许是生活在这一区域的游牧民族。
从“胡气”的象征到权威的标志
虽然也有些不同观点,但汉人主导的中国史观对长靴的来历大体与上述的考古发现一致。古汉人相信,长靴是“古西胡”的作品。战国时一个被称为赵武灵王的北方诸侯君主为了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决心在服装上也模仿胡人,于是引进了一种黄色的短筒靴。而通过对年在沈阳发现的一处战国墓葬的发掘,人们相信这个时代的军人也穿上了镶满了铜泡的名副其实的长筒皮靴。就这样,原产于胡地的长靴皮靴作为军用品被引入了汉地。在骑马时靴筒便于夹紧马肚,随着季节变化夏可防蚊冬可御寒,还有些防水功能,于军人尤其是骑兵而言,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便利的东西。
尽管如此,此后很长一段岁月内,长靴依然颇受汉人文化观念的抵制,被视为“胡气”的象征。从实用角度说,与长靴配套的是合裆裤。这种裤子同样与汉人传统的“上衣下裳”和开裆裤发生着文化冲突,套在上面的长统靴自然也是不方便上台面的东西。于是到南北朝时代,当北方已经满是长靴胡人时,以汉人正统自居的南朝,依然坚持不让穿着长靴的过分时髦人士上殿。“着靴垂足”的侯景,在正史作者眼中,根本就是个无可救药的野蛮人。
受胡人影响颇深的北方汉人建立了隋唐全国政权。长靴的地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不再仅仅是军人的“野战装备”,还登堂入室成为官员的正式服饰组成部分。于是军人也穿靴;官员也穿靴;财主商人们也穿靴;敦煌壁画上甚至农民也穿着长筒黑靴。不过考虑到唐代畜牧业并不算特别发达的事实,笔者倒是更倾向于认为这个农民也许只是把他服兵役时代穿过的靴子带回了家。唐代女人穿男装很常见,穿长靴同样常见。
隋唐时代的长靴外形非常有意思。喇叭口的靴筒非常肥大甚至有些难看(唐代笔记中关于在靴筒里放各种乱七八糟匪夷所思物品的记载显然是有依据的),靴面倒是很精致小巧,前面有个用以钩住马镫的翘尖。这玩艺的学名叫“靴鼻”,除了前述挂马镫作用外,它还有个特殊功能,就是穿在位高权重者脚上,让马屁精们抱着“嗅之”(或者“吮之”)。据说西方最早的“恋靴”描写来自法国作家左拉于年发表的小说《黛莱丝·拉甘》,而“舔征服者靴子”的说法最初是何起源却不甚清楚。但在多年前的中国,这个玩法就已经存在了。另一个与长靴有关的玩法是让地位低下者为高贵者脱靴,在唐代这样的事例并不仅限于李白和高力士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
显然,在唐代,通常是涂成黑色有时还会被处理的漆黑发光的长筒靴,已经从南朝人心目中的蛮夷标志,变成用以展示穿着者权威或者征服者地位的象征。唐代以后,长靴作为官服标准配备的地位被历朝历代所延续。在畜牧业不大发达的古中国,长靴无疑是一种奢侈品。其“官员身份象征”的属性也越发强烈,以至于有了“穿靴戴帽”之类的说法。到了明代,官方甚至一度禁止平民穿靴(但有地域区别)。清代对长靴的穿着也有诸多限制或禁止命令。另一方面,在唐代一度极为风行的女性穿靴习俗,随着宋代以来小脚的盛行,则是越来越稀少了。
就长靴本身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变得越来越难看。尤其是靴面越来越肥大且厚底。后者大概是步行的需要(但军事用途的薄底靴也存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明清两代流行缎面靴,加上戏剧的影响,使得现在很多人误以为古人穿布靴为主,根本不知道皮靴才是主流的事实。
马靴直接见证了冷战的成败
长靴在西方如何起源并不特别清楚。似乎古希腊时代就有了短筒靴。蒙古西侵据说也把亚洲式的轻便靴带到了欧洲。长期以来,东欧似乎比西欧更流行长靴,尤其是东欧女性远比西欧更多穿着长靴。这或许与蒙古人的影响有关。但到了拿破仑战争前后的近现代,欧洲军队却不分骑兵步兵还是长官下属,都普遍穿着长靴。肥大的靴筒有时被填充上稻草以御寒。现代皮靴的外形基本就是这个时代奠定的。黑森雇佣兵穿着扎眼的过膝长统马靴去了美洲,据说是现代美式牛仔靴的前身;19世纪以来,追求近代化的亚洲军队,也穿上了西式马靴——虽然一般只限于军官和骑兵。而在民国时代,很多中国骑兵依然穿着蒙古式传统长靴。战争再次推动了长靴的发展和普及。
到了日俄战争,打着绑腿的日本陆军击败了穿着低帮线长统靴的俄国陆军。在炮火和机枪火力越来越密集的时代,古来艳丽的军服变得越来越灰暗朴素。对步兵而言,无论行军还是行动,绑腿都要比笨重的长筒靴更实用。至于最需要长靴的骑兵,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来日本陆军骑兵在战地就不怎么穿长靴而改打绑腿。就这样,随着骑兵平端长矛或高举马刀横扫战场时代的一去不返,马靴的实用功能也黯然失色。当然长靴也有了新市场,特别是某些技术兵种:如飞行员、坦克手和摩托车手等等。
但在二战时代,苏联和德国军队的步兵单位依然普遍采用长靴。俄国军队坚信,在泥泞肮脏而且遍布沼泽河流的战地,长筒马靴依然是实用的。它令士兵们毫不犹豫地跨过一切障碍。但在实际中,出于物资短缺等原因,很多苏军也打上了绑腿。
★以下二战中的军靴★
穿长靴的德国党卫军。从左至右:党卫队三级小队长兼鼓手;血旗旗手;党卫队二级小队长
打绑腿的日军。从左至右:高砂游击队;伞兵,第2突袭旅;志愿兵,义烈空降部队
德国东线盟军装备。从左至右:代理中士,匈牙利“圣拉迪斯劳斯”师;少校,罗马尼亚近卫骑兵团;一等兵,意大利黑衬衫部队
同一时期,长靴作为军官标志,基本各国都配发。与按固定尺码配发的士兵马靴不同,军官长靴往往是量身定做。但各国军官对马靴的兴趣也各不相同。美军除了一些爱出风头的军官和军校生以及骑兵,就很少穿长靴(如史迪威甚至有些讨厌长靴)。这似乎和美军当时标榜“平民化”的风气有关,却并不妨碍巴顿这种讨厌平民化的人穿着马靴招摇过市。虽然日本陆军军官的标准长靴是黑色的(样式很像利于步行的俄式马靴),但黄色骑兵长靴似乎更受欢迎,穿着者也未必都是骑兵。而一旦进入战地,日军军官往往也把马靴换成绑腿。二战时代,绑腿几乎成为亚洲军队的标志。充分证明了当时亚洲的贫穷:既穿不起苏德的长靴也穿不起美式短靴,更没有多如牛毛的机械化运输工具,只能打上绑腿靠两条腿走遍天下。
苏联红军哥萨克骑兵。从左至右:上尉,库班哥萨克;军官,库班哥萨克;中尉,捷列克哥萨克
着帆布护腿和短靴的美军。从左至右:诺曼·柯达将军;小西奥多·罗斯福将军;美军奥马尔·N·布莱德利将军
英军装备。从左至右:中士,陆军摄影和摄像部队;滑翔机机降步兵,第6空降师德文夏团第12营;工兵,皇家工兵部队第野战连
冷战时期,形成了西方阵营普遍穿美式短帮军靴;东方阵营中的欧洲系国家普遍穿长筒靴;而东方阵营中的亚洲系国家偏爱胶鞋的三足鼎立局面。长筒靴成了欧系东方阵营的标志(以苏联和东德为代表)。因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和日本陆军军官流行穿着长靴,西方阵营利用这一点做宣传,把欧系东方阵营描画成类似纳粹的形象。比利时著名漫画《丁丁历险记》中,影射苏联和东德的虚构国家“博尔多利亚”,就无论官兵都穿着长筒马靴。后来冷战结束东方阵营失败,东德不复存在,俄国军队也取消了野战部队的制式长筒马靴。无形中,马靴竟直接见证了冷战的成败。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形成一个奇特文化现象:长靴在西方被描画成“纳粹和邪恶共产阵营”标志;在亚洲东方阵营特别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中,长靴又往往和“国民党官老爷”或者“洋鬼子”联系在一起,而被打上“剥削阶级”“压迫阶级”的烙印。当然也有例外的正面描述,比如“大马靴叔叔”或者北方少数民族形象。虽然没有任何国家和军队发出明文禁止,但长靴的确被赋予过多负面文化形象,以至于民间男性越来越少穿长靴。
另一方面,在女权运动催生下,原本在西方就很流行的女性短靴,在战后逐渐被男性化的长靴所取代。中国内战时代张乐平创作的一张三毛漫画上,就出现了穿着半长筒靴的贵妇形象。60年代走红的美国女歌手南茜·辛纳特拉不仅本人极爱穿长靴,还在歌曲中把长靴描绘成女性独立的象征,进一步推动了女性长靴在美欧日本的流行。时至今日,女性穿靴越来越普遍以至成为主流,而男性穿长靴倒成了非主流。但也有例外。二战后,一个曾服役于芬兰陆军(也是一支配发马靴的军队)的同性恋画家“芬兰的汤姆”,用他的画笔推动马靴成为同性恋文化的标志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后一度盛行的科幻漫画中,长靴在民间的普及被视为未来服饰的发展趋势,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