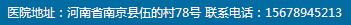当前位置:鼻肥 > 鼻肥大治疗 > 除了相声和煎饼果子,天津还有什么 >
除了相声和煎饼果子,天津还有什么
五大道、海河、相声、煎饼果子……这是你印象中的天津吗?对于出生在天津的建筑师朱起鹏来说,绝非如此。
从清晨热闹的早点摊开始,朱起鹏带着大家探访了天津清真南大寺、西开教堂、黄家花园、文新里、张园、安里甘教堂和浙江兴业银行旧址。从明代因漕运兴起的城市起点,到清末民初的九国租界,再到最热门的网红打卡地,时间跨越五百多年。面对这个所谓“万国建筑博览会”所在地,其实新与旧、真与假混杂的城市,他有某种陌生感,不过,“所有新的都会变成老的,那些人们臆造的景象,也会变成我们真实的记忆。”
三联人文城市奖从年开始,于每个城市邀请一位建筑师或城市达人,挖掘私家行走路线,探寻个人视角下的城市秘境。拆开这一个城市“盲盒”,里面藏着的也许不是精美的礼物,而是味道、回忆、秘密和意外。
一个人×一座城:朱起鹏和他的天津文|朱起鹏编辑|沈思、李明洁让一个很久不住在天津的天津人介绍天津,这个难题终于摆到我的面前。其实除了偶尔回去看看爸妈,我连张天津的公交卡都没有。我出生在这,成长在这,已经30多年了。很多东西早以司空见惯,你会发现外地人对天津的认识,似乎还是包子、麻花、煎饼果子,以及希望你随时能来一段的相声。朱起鹏客观地讲,天津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变得在北方城市中默默无闻。除了偶尔的负面消息之外,你似乎都忘了在北京的东面,还潜伏着一座近万人口的大城。朱起鹏的天津城市地图(朱起鹏绘)一日之计,在于果子郭德纲有段揶揄天津人的玩笑,说在天津人心中“最好吃的东西是早点,世界的尽头在杨村。”这包袱甩出来,底下乐得捶胸顿足的一定是天津人。何尝不是呢,我们小时候,到杨村,现在叫武清区,就得坐火车了,公交是到不了的。对于恋家的天津人来说,那就和去外太空差不多。
我生在西关街的一个小院里,包衣还埋在那院子的门槛下。这里离外太空有一定距离。但距离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早点,特别近。西关街早点的兴盛,几乎和这座城市的诞生同时。大概5、年前,一些穆斯林沿着京杭运河跑到建成不久的天津做生意,他们在城市西门外的洼地上盖庙建房,形成社区。穆斯林精致的饮食方式,影响了运河周边的老百姓。如今清真南大寺周边的街巷里,各种餐饮小吃的铺子鳞次栉比。西关街一带成了天津美食的源头之一。上世纪90年代的西北角清真寺说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早点,一点不假。您知道的天津包子、麻花、炸糕和煎饼果子嘎巴菜,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早点。早餐本身是一天中最仓促的一餐,天津人却弄得特色鲜明。同样是面粉,可以炸成果子,可以炸成果篦,还可以和上糖油面,做成糖皮儿果子。还能把果子做成个小口袋,往里面灌鸡蛋,称为炸荷包。最后,把这它们用面粉烙成的大饼一卷。一顿完美的早餐,就在单一的碳水循环中完成。炸果子今天看来,似乎挺不健康的。但这的确是匮乏时代天津人的伟大发明。我们家年搬离西关街,此后的几十年里,我爸一提到那儿就会说起生我那年,他用大饼卷着7根油条蹲在路边三两下吃完的事迹。如今的西关街,小胡同都拆除了,80年代末建起了居住小区。但人们的生活习惯还和住胡同差不多。这里可能是最贴近旧时天津氛围的街区。那些最好吃的炸果子、摊煎饼、做噶巴菜的摊子也依然存在。很多人会坐上2个小时的公交车来这吃上一顿,但一眼望过去,很多都是老人。在西北角吃早点的老人说这么热闹,西关街的一切,其实都在我产生记忆之前发生。我听说有人能记住自己一两岁时的事,可惜我不行。我让妈妈回忆当年小院的情况,她长篇大论的说着我不曾知道的人和事,甚至一笔一划写出了每个邻居的名字和居住的位置。这里的一切,都曾在我身边真切的发生,却没有任何东西留在我的记忆里。不知为什么,突然有点想落泪,那些鲜活的生活,如今只剩下我妈自顾自的念叨。我根据母亲的描述和老照片复原的九天庙胡同小院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情况大教堂是怎样一种存在我上小学时,搬到了西开教堂后身的一个小区里。选择那个小区,因为离我姥爷家很近。小时候去姥爷家玩,总能隐约听到外面叮叮咚咚的钟声,那时我不知道这钟声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来自哪。后来见到楼群间西开教堂高耸的罗曼式钟塔。啊,一下次确信了这动听的声音,一定是从那伟大的建筑中发出来的。
搬到这里后,更笃信这地方神奇的力量,那时天津已经有了不少高楼,但西开教堂依然是周边最重要的地标。它建成于年,以法国马赛的主教座堂为蓝本,是华北当时最大的教堂。西开教堂雄踞旧法租界的核心,一条滨江道以它为底景,串联起无数华丽的公共建筑,直达海河岸边,当时应该是个很有雄心的规划。上世纪90年代初的滨江道,底景为西开教堂,近景为劝业场、惠中饭店等商业建筑,这曾是法租界重要的城市轴线。小时候没有所谓建筑的概念,只知道房子。而西开教堂却不是普通的房子。它无疑是美的,虽然这美我形容不出来,但一定有某种东西赋予了它力量。我的初中在天津一中,离教堂不远,每天我会穿过教堂巨大的侧影上学和放学。那时人们还能径直走到教堂神坛外侧的墙根下,目睹厚实的米黄色砖墙高高托起绿色的穹顶。砖墙下是一片花鸟市场。奇怪的是,我却回忆不起那座市场的任何声音,也许在教堂的侧影下,连草虫和小鸟都安静下来了吧。上世纪90年代的教堂后身,这条小街曾是花鸟市场,90年代末拆除长大一些,我发现那阵时常听到的钟声,其实是不远处一座电报大楼发出的,它也并不是什么钟声,而是段东方红的报时曲调。真相已经大白,但我仍然原意相信,那罗曼式的高塔里,一定曾传出过这世上最美的钟声。路边西餐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天津人和西餐从来没有什么隔膜。比如,我很小就听到母亲和她的同事谈论沙拉的做法和诀窍,只不过她们口中的沙拉,是天津口音浓重的“萨辣子”。在老天津人的语言系统里,最后那个“拉”如果不跟上个“子”,变成“辣子”,仿佛就不像人话似的。
当然,这个所谓“萨辣子”,丝毫不辣,而是某种俄式土豆沙拉的变体。我还曾听到一个朋友谈论天津菜“全爆”的做法。他说这种白汁浓稠的爆菜,其实来自西餐的奶油焗。也就是说,用虾仁、鱿鱼、鸡丁炒制的全爆,其实是奶油焗海鲜的变形。如果真是如此,那天津菜和西餐的关联真是不浅。作为曾遍布租界的城市,西餐在天津有过很多名店,比如营口道上的大华饭店,解放北路的DD饭店。现在依然存在的,还有小白楼的起士林。上世纪80年代末的小白楼起士林餐厅比起这些和西方很接近的洋餐厅,我更怀念那种街边就能买到炸猪排、沙拉子和奶油蛋糕。我的初中在原先的英租界。我上学的时候,那里已经没什么英式生活的痕迹了。但沿着西安道一直向东,却有大片的旧洋楼和公馆,其中一段路称为黄家花园。我对黄家花园印象模糊,但那里的第二游泳池我却是常客。游泳结束,饥肠辘辘,到街边买个炸猪排或奶油蛋糕,抑或是装在塑料饭盒里的意大利面,可以说是相当潇洒的享受了。今天的黄家花园,洋楼拆了一多半,街道似乎也没有之前整洁。但涌现出很多所谓的路边西餐。虽然它们自称老店,但我之前好像没怎么见过。当然,你依然能选择在路边蹲着吃。至于口味,那就见仁见智了。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爸蹬着28自行车,用不锈钢饭盒从某个西餐馆子打来巧克力冰淇凌。化了一半的冰淇凌混合着不锈钢饭盒特有的气息,也许才是我对天津西餐的真实感觉。散步乐园让我推荐一处天津的散步乐园,毫无疑问是旧时的日租界。当然,之前我也没有什么日租界的概念,我只知道从我高中学校出发,往任何一个方向走上几公里,都是连绵的林荫路和各式各样的小洋楼。
我高中在第二南开中学,那里80年前,曾经是日租界的松岛女中。松岛女中在当时堪称先进,以至于到我们上学时,那八十多年前的主楼,依然是学校里最好的建筑。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原址(今天津汇文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前身,建于年的松岛女子中学日租界范围不小,从现在的南京路一直到海河边,都是它的属地。不同于其他租界,日租界在建筑风格上没什么限制。日本式的、地中海式的、托斯卡纳式的、摩登式的,还有些老楼明明八九十年了,却带着鲜明的现代主义味道。原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建筑它们都按照日本都市挤挤插插的条町式排列着。走街串巷,总能发现很多设计得很巧妙的房子。它们在有限的空间里,别致的安排了功能和形式。这里的人们,生活距离更近,鸡犬之声相闻。比起英法租界那些堂皇的欧式大楼和别墅,别有一番趣味。日租界的西北部,有一条长长的鞍山道,那里集中了民国时很多要员的住宅,比如溥仪的静园,孙中山曾经下榻的张园,还有段祺瑞的公馆。段公馆当年是和平区教研室,我一直认为那里汇集了全宇宙的特级教师。当时有个物理提高班在它的后楼,招收各校所谓的尖子生。我有一次超水平发挥,也混迹其中。每次去上课,都有种荣誉获奖的感觉。那时的后楼是个现代式的楼房,但层高反倒要矮一些,在三层阳台基本只能看到老楼的二层。透过那些旧式的巨大木窗,我看到老楼里一张张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和桌子后面的戴着大眼镜的老师,对我来说他们简直都是天神下凡。今日段祺瑞故居我当时有种很二的想法,觉得这些老师要是能经常看到我,心里就会记得“噢,这家伙是个小天才。”所以我就在后楼的阳台上,抽一切时间努力和他们对视,结果一个看我的都没有。段公馆南面还有座张园,之前是少儿图书馆。当时觉得里面设施很旧,楼里每个位置似乎都在返潮。而且到上高中时,我已经不屑再去这种标有“少儿”的场所了。那时总传说张园地下有座日本人的地牢,传的神乎其神,等我们鼓起勇气决定去探访时,少儿图书馆就关闭了。张园整修后现在,这些府邸已经相继修复完毕,并逐步对外开放,但那些过去的印象,有时还会在眼前闪回。不同于英法租界,日租界的历史地位比较尴尬。到今天也只有鞍山道和陕西路的一小片被列入保护的范畴。至于甘肃路、哈密道、锦州道、河南路等多数区域,虽然价值很高,但仍被当作破旧街区看待。关于这些地段拆除的消息和规划,也此起彼伏。原天津日租界鸟瞰从历史的角度说,天津日租界既是侵华战争重要罪证,也是天津近代都市发展的生动案例。今天它依然是城市名副其实的downtown,是它最具生活氛围和都市情调的区域,这里不但有众多名人故居,也有全国驰名的文玩市场,以及许多藏在巷子里的宝藏餐厅。我希望那些曾深深打动我的城市空间,能被这座城市的人们继续看到。老房子怎么穿越时空高中的后半段,我们的学校迁到现在南门外大街的校址,我家也搬到五大道的南面。上下学的路程拉长了,需要横穿整个日、法、英三个租界。当然,这也是我事后总结出来的。当时无非就是挑一些有树木遮荫,街两侧有看头的马路打发路上的时间。
现在想想,那时也挺好玩,我时而会转到劝业场一带的浙江兴业银行,当时它已改成永正裁缝店了,但去营业大厅里摸摸石雕狮子的大柜台没人管。或者转道泰安道老市委那边的安里甘教堂,往传说中的鬼宅里扒扒头。但我最喜欢的一条路,还是大沽北路。大沽北路原来称为海大道,似乎从乾隆年间就存在了。海大道么,直通大海,从天津县城直达海边的大沽镇。19世纪末英国人占据此地,修路建屋。年的海大道(今大沽北路)我印象里的大沽北路,两侧是各式高大的洋楼,与隔壁的解放北路不同,这里的洋楼形制朴实,没有很刻意的装饰,用现在的观点看,就叫具备结构理性和形式逻辑。大沽北路中段有座先农大楼,上中下三层分别用了不同的窗型,非常别致,街道也恰好在这个位置拐了个浅浅的弯,街景非常美。年拆除前的大沽北路,远景为先农公司大楼(朱起鹏摄)这条路是林荫道中的林荫道,高大的白蜡遮天蔽日,下雨天完全不用撑伞,盛夏酷暑,骑到一半累了,蹲在大沽路菜市场(我妈一直叫它“英国菜市”)门口的浓荫下,来一瓶冰镇山海关,再没有比这更惬意的时刻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路都是我的保留节目。我会带着暗恋的女生一遍遍地走。其实她家住河东区,这么走得多绕4到5公里,陪有特殊癖好的人一遍遍刷这条街,也是难为人家了。如今浙江兴业银行和安里甘教堂,都已精心修复完毕,植入了新的功用。成了城市中的网红景点,而大沽北路得绝大部分,在我上大学的那年被拆成了平地。整修后的浙江兴业银行这条路今天还残留了一小段,在原来老市委花园的位置。在那仅剩的大沽北路上,你能看到古典复兴的开滦矿务局、折衷式的仪品公司大楼,现代式的基督教青年会和纳森居住的中式四合院,这里有我熟悉的天津,并不拘泥于某种形式与风格,建筑只是业主形成空间和功能的手段。不同的模式相得益彰,可能这才是所谓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吧。老街的对面,已经被拓宽为双向八车道的大道,道边是新建不久的大厦。可能为了和历史环境协调,它们都被妆点成想象中的欧式风格。有时我会想,如果大沽北路今天还在,会怎样呢?如果那些美丽的房子也被如兴业银行或者安里甘一样对待,这座城市的面貌又会是怎样呢?整修后的安里甘教堂历史没法假设,城市的发展也没法回头。如今的场景也许在多数人看来并无不妥,反倒是那段窄街显得有点碍事。出于职业的习惯,我总喜欢把真实的历史遗产叫做“真的”,那些模仿的建筑叫做“假的”。但对于建筑来说,并没有“真假”之分,它们都能承载或美好或糟糕的生活。如果说区别,大概只能分成“新的”或者“老的”。在城市里,这些“新的”,早晚也会变成“老的”,当“老的”全部消失,“新的”也就没什么不妥,它们自会重新构成新的历史。想到这里,突然觉得好受多了。教堂前的“米老鼠”(沈思摄)和摄制组拍摄西开教堂时,我们在教堂的广场上,看到一个真人扮演的米老鼠,盛夏的中午,广场上空无一人。他套着卡通头套,呆立原地无所适从,时不时又突然摆出几个姿势。我对这个城市,大概就像这只站在教堂前的米老鼠,沉浸在自己预设的场景里,很想努力进入角色,但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频道。嗯,好在他是一个爱这座城市的人。三联人文城市奖是由《三联生活周刊》首次发起主办的建筑/城市评奖。中国城市化进入存量时代,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节点上,城市必将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发生更加密切关系的关联。然而在当下,公众对于城市的公共性,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审美、功能、权力意识都相对薄弱。我们期望借此推动公众启蒙,激发公众参与,推动未来中国城市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的主题设定为“重建联结”,以回应在社交隔离之后,如何回到人与人的交往和关联。更多有关三联人文城市奖的评奖及相关活动进展,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