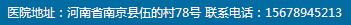当前位置:鼻肥 > 鼻肥大病因 > 艾凤荣薪火传承,只为ldquo看见 >
艾凤荣薪火传承,只为ldquo看见
医院垂体疾病MDT团队访谈
题图为我国神经视野学的奠基人劳远琇教授的学生艾凤荣老师
编者按
“眼球好比是电灯泡,视神经纤维好比是电线,大脑视皮质好比是电站。人们的眼球接受到外界物体发出的各种信号,经过视神经纤维传到大脑后,形成物象由大脑识别东西,而眼球本身并不能看到、识别东西。灯不亮,不一定是灯泡坏了,可能是电线或电站出了毛病。同样的道理,眼睛看不清东西,不一定是眼球有病,很可能是视神经纤维的某一部分出了问题。”
这是劳远琇教授年以浅显易通的比喻阐释了什么是神经视野学——研究视神经与视功能缺陷之间关系的科学。
图1.劳远琇
当眼球固定向前平视时,眼睛所能看到的最大空间就是视野。人眼球视网膜里层有上百万个神经节细胞,它们各伸出一丝纤维,这些纤维汇合到一起成为视神经。当不同阶段上的视神经发生病变或有了障碍时,眼睛会出现部位不同、范围不同的盲区,通过视野检查把这些盲区标记下来,就可以绘制出视野图。视野检查是一种物理和心理的检查。
对于垂体瘤而言,尤其是在对该疾病的认识尚浅、诊断技术不完善时,视野检查可以帮助找到垂体瘤。更重要的是,很多情况下检查结果不但是首发诊断的判据,而且能够为垂体瘤的手术定位提供参考依据。
为了深入了解神经视野学在垂体瘤诊疗中的作用和意义,笔者专访了我国神经视野学的奠基人劳远琇教授的学生艾凤荣老师。
艾老师与劳远琇教授共事逾三十年。
前言
年,劳远琇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期间首次接触到神经视野学并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年回国后来到协和,医院第一位全职眼科医生。年,在罗宗贤教授的建议和鼓励下,劳远琇在协和组建了当时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神经视野学专业组,自此,她全身心的投入到了神经视野学事业中去,逐步填补了我国在视野学领域的空白。
“......(上世纪70年代)一次,外地来参加培训的一名眼科主任说‘我快50岁了,手发抖、眼也花,做不了手术了,我也想改行做视野。’当时,劳大夫饶有风趣不客气地说‘我不是年龄大了,眼花了,手抖了才做神经视野,我三十几岁就开始做了’。”
——采访那天,艾凤荣老师极其自豪的又跟笔者补充道:“劳大夫手术做的很漂亮的,她是来补充空白的。”
艾凤荣老师回忆,医院大概仅有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尾声,在时代大背景下,医院“掺沙子”,自己就是年“掺”到协和的,卫校学习两年,年毕业进入眼科,年到门诊,自此,一直跟随劳远琇教授,直到劳教授年因病离开临床。
与劳教授相识时,艾老师刚二十岁出头,和劳教授女儿年龄相仿,对学术、学科都还懵懵懂懂。“劳教授工作中要求严苛,但生活中和蔼可亲,待我就像待自己的女儿一般,早年她给我起了个昵称‘姑奶奶’。”四五十年过去了,艾老师跟笔者聊至此,对劳教授的孺慕之情流露无遗。
艾老师说“从查出第一个视野图起,就深深喜欢上了神经视野学。”
01“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劳大夫就对垂体瘤有了深入研究。”
神经视野学与人体多个器官联系广泛,除了与多种眼球本身的疾病有关以外,与颅内疾患和周身中毒性疾病的关系尤为密切。
视野的改变可能与视觉形成传导路的每一个环节有关,“可能是电灯泡、电线、电站中的任何一个部件损坏了”。其中与视神经、视交叉损害(“电线”损坏)相关的疾病里包括垂体瘤。艾老师在学习神经视野的过程中,垂体瘤病人的视野改变是令其印象格外深刻的疾病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劳教授基于颅内解剖学知识,结合视神经走形和视野分析,发现了垂体瘤病人的视野改变,在劳教授编著的国内第一本视野学专著《临床视野学》(年出版)中有详细描述。
图2.劳教授年的专著《临床视野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垂体瘤的诊断水平有限,国内尚无CT、MRI等影像学诊断技术,除了X光、脑血管造影和气脑造影可以“模棱两可”地“看见”垂体瘤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影像学上的办法可以“看清”垂体瘤。
诊断水平的滞后加上对垂体瘤的认知不足,大部分垂体瘤在发现时都已是晚期,并且病人往往是以眼部症状、内分泌症状或头痛呕吐为首发症状到眼科、妇科、神经内科就诊。在那个年代,约半数以上的垂体瘤病人会有视野缺损,眼科会收诊到很大一部分已患有垂体瘤的病人,视野改变很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首发诊断依据。
当时的观点认为如果患有垂体瘤,随着肿瘤生长,并向上伸展,压迫视神经和视交叉,从而导致视野缺损。“如果不及时找出病因并进行治疗,视野缺损会逐渐扩大,伴随视力减退,甚至全盲。”
尽管劳教授已发现了垂体瘤的视野改变规律,但是根据视野的临床表现“诊断”垂体瘤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实际碰到的病人在临床表现上往往个体差异大,很容易遇到“不寻常”的情况,给临床诊断增加了难度。为了更好的探究垂体瘤的诊疗策略,早年劳教授会时常跟当时的尹昭炎、史轶蘩、王直中教授等进行讨论,其实这种会诊的模式和方法是后来垂体瘤协作组(年成立)在一定形式上的雏形。
图3.劳教授当年的笔记本及垂体瘤早期视野图
劳教授还是第一位垂体瘤卒中的发现者。“劳大夫自我要求严格,不放过对任何一个疑难病例的考究,垂体瘤卒中就是她深入研究一例病例后发现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位年轻男性病人,临床症状以剧烈头痛、呕吐为主,医院诊断为脑膜炎,曾经过大量治疗,但病情未有好转,后来几经周转来到协和眼科,查了视野。由于是不典型的垂体瘤视野改变,劳大夫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详细总结与该病例有关的各方面资料,并整理备课,参与当时的会诊不仅有协和的大夫,医院的王忠诚教授,经过深入讨论,劳大夫认为该例是垂体瘤卒中,自此,才有了‘垂体瘤卒中’的概念。”
在国内影像诊断技术、病理学研究均尚不发达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劳教授已经对垂体瘤有了很深刻的认识和研究。
02“大家都因跟着劳大夫学习而感到自豪。”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劳教授为了增强艾凤荣老师和高老师(从天津来的一位年轻进修医生)的神经视野学知识,每周四下午等大家出完门诊,四点以后,劳教授会给他俩进行小范围的讲课。
“后来,逐渐影响到了科里的其他人,包括研究生和外地的进修生,再后来,全国各地的医生都会来跟着劳大夫学习神经视野。每个周四下午劳大夫雷打不动地给大家‘开小灶’,几十年如一日,直到她因病离开临床。劳大夫学术渊博,待人和蔼,大家都因为跟着她学习而感到自豪。”
劳教授每次讲课都会特别用心地备课,手把手地教,哪怕只有几个人,也会非常仔细地讲解每一个知识点,深入浅出,有条不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时候,大家学习热情高涨,对神经视野学的知识如饥似渴,听的都非常认真,甚至会要来劳教授的笔记认真记录。“劳大夫讲同一课题,听过一次,以后再听一次,必有新的收获。”曾经跟劳教授学习眼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的医生。
图4.劳远琇教授与同事和学生们(二排左二为艾凤荣老师)
“为了给学生更生动、透彻地讲解,劳大夫经常用课余时间从大量病例中挑出典型案例,亲自画视野图、配文字,医院的图片室拍照,再将胶卷放到幻灯片模块里,在原始的幻灯仪上放映。医院非常鼓励将临床资料以图片的形式保存下来,但制作一张幻灯片真的非常费时间。到后来有了计算机,现在有了PowerPoint软件,做幻灯已经简单多了。”
图5.早年的幻灯片
协和老一辈大夫,都是一心扑在临床和科研上,没有加班的概念、没有周末,没有休假概念,没有奖金,也不讲价钱。对待患者更是“一条龙”式的服务,比如眼科“根据视野的临床表现,考虑是垂体瘤”,都会赶紧为病人“写条儿”,标明让病人去找谁,“请神经外科任老/苏老会诊”,病人拿着条儿去了,任祖渊和苏长保教授真的会立马给病人加号。
03“劳大夫教会我们如何‘看见’垂体瘤。”
艾老师说“因视力问题来眼科就诊的病人,我们在排除了眼球本身的问题以后,通过视野检查,就可以推测病人是否有垂体瘤。”
当然,那时候,会有一部分垂体瘤的病人被误诊、误治,直到病人有机会接触到视野检查,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治疗。
例一,这位病人曾被误以为是精神病。
“一名来自东方歌舞团的打击乐手,男性,40岁,因文革时候被戴“臭老九”的帽子,受了冲击,一向寡言少语的他突然变得精神兴奋,医院接受多次休克治疗。在治疗期间反应自己眼睛模糊甚至要“看不见了”,开始认为是镇定剂所致,后来家人带他来我们科,当时排除其他眼部疾病后,我为他查了视野,通过分析认为是垂体的问题,因此建议他到放射科进行影像学检查,最后确诊为垂体瘤,后来接受手术切除了垂体瘤,视野也变好,他现在仍在世。”
例二,这位病人曾被误以为是神经炎。(见图6)
“一名北京师范学院的女性,孕前曾闭经,孕后出现视力下降(女性妊娠时,生长激素高于正常人,垂体会出现生理性肥大),妊娠7个月时,视力严重下降到已几近失明,曾在外院接受视神经炎相关治疗,效果不佳。后来到我们科,我帮她查的视野,视野图显示为非常小的管状视野,提示是垂体瘤。当时她却非常高兴,因为查明了病因。后来妇产科、神经外科、眼科、内分泌科等一起参加了她的病例讨论,主要围绕‘先生育还是先进行垂体瘤切除挽救视力?’会上妇产科林巧稚教授非常果断的提出‘切除垂体瘤、挽救视力第一,神经外科与我们妇产科一同上手术台,先进行垂体瘤切除。妊娠7个月,胎儿已经能够成活,如果手术期间出现宫缩,产科随时准备上台’。手术非常顺利,病人术中未生产,术后顺利生产。”
图6.北京师范学院怀孕女性的视野图图
有一次在门诊时,一个家属带着病人来看病,劳大夫跟这位家属说“您什么时候有空,来找我看看吧。”“我没有病,我是带家人来看病的。”“没有关系,我哪天有门诊的,您过来看看吧。”后来,这位家属回家后应该是认真思考了劳教授的话,果然找劳教授来了。经过视野检查,发现果真是垂体瘤。事实上,有的垂体瘤是有一些体征的——鼻子高大、下巴弯、额头翘、手指短粗、说话声音吭哧吭哧的等(肢端肥大症)。
自这次“看相”后,还闹过一次笑话。半夜,邻居家老太太领着自家两个小孩敲劳教授家门,说“听别人说您会相面,帮我们家小孩儿看看吧,他俩不爱吃饭。”
艾老师不由得回忆起自己帮同事“看出”垂体瘤的经历。并满怀思念之情感慨道“每当查出病因的时候,尤其怀念劳大夫,如果劳大夫在,就可以请教她了。”
“一位同事,毕业后就来了协和,结婚,生子,大家是看着她长大的。生育完以后,我发现她鼻子越来越大,当时感觉她应该是有问题的,因此建议她查了视野、CT,结果的确是垂体瘤,无功能性垂体腺瘤。后来,神经外科的任祖渊教授给她做的手术。当时,任老还跟我感慨‘小艾,燕儿的垂体瘤位置不太好,正好卡在了视交叉和海绵道,手术肯定是切不干净的。’手术后,她的面容改变许多,鼻子没那么大了。
后来科室的人还跟艾老师玩笑说“跟劳大夫学得会看相了”。
在劳教授的研究和指导下,神经视野学从无到有,逐渐完善。在垂体瘤方面,已经帮助垂体瘤的诊疗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协和已经配备了CT,影像诊断水平的进步,使有人会误认为CT诊断可替代视野检查,劳教授每每都会纠正——二者是相辅的。比如对于垂体瘤而言,视野检查可以表明视功能损伤的多少及推测病灶所在的位置,帮助手术进行定位。
04“劳大夫教导年轻人时,点滴入微,精益求精。”
艾老师说,与现在相比,那时候视野检查的条件很艰苦,手工制作的小视标在原始视野屏上要一点一点移动,手动为病人检查视野。病人需要坐在离视野屏1米远的距离,眼睛盯住视野屏中心的小白点用眼睛余光看视标,以确定视野的范围,判断视野是否有缺损,视野图也是手画的。
图7.s手工制作的视标
视标是在劳教授的指导下,当时科室的王子政老师(已故)带着艾老师制作的。每根视标的柄内都是铜丝,外面包裹常规医用白色胶布,细铜丝外面的胶布不能相互压边,必须用手指甲慢慢将胶布对的严丝合缝对接,再反复涂多遍涂漆。视标最两端是用锤子砸压而成或是焊接上的,尺寸要经过精确测量;红、白、黑色漆是艾老师四处跑到装修人家那里要来的、不能用反光的漆。最大的视标是20mm,最小的是1mm。
艾老师回忆,那时劳教授总是强调,查视野时“医患双方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跟病人讲明白了他才会配合,因为只有病人配合了,才能查出真正的问题所在。查视野最终要的是图形,而不是“大黑疙瘩”或者向心性缩小(这两种视野图都说明不了问题)。“因此,查视野的时候必须做到不厌其烦,不停地说,并注意时刻观察病人,通常一个上午也仅能查五六个病人。”此外,还必须看病例、了解病史、查完要确认是否与眼底病变和主诉相符合。
要用大白话与病人沟通——不能说“用眼睛的余光看”。
您看到中间这个小白点了吗?
-看到了。
盯住它,不要动。看到旁边小棍了上的小红(或为白色,视标的颜色,有大小之分)点了吗?
-嗯。
什么时候看不见了,你就告诉我,可是呢,眼睛不要跟着它(小红点)走,不要找它。
因为对于一些专业术语,不仅文化程度稍低的病人,就算高学历者也不一定懂什么叫余光。
图8.30度中心手查视野屏
注:当年,劳远琇教授设计、用黑绒布手工制作的视野屏,至今仍保留在视野室。艾凤荣老师仍会不时用它来教学,为视野机难以查出的视野或者为不配合的小孩查视野。
艾老师补充,在检查视野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细节。
“有一次,已经成为院士的史轶蘩教授拿着病例风风火火亲自跑到眼科门诊找到我,质问‘这个视野是怎么查的!CT查出来是往蝶窦走的,并没有影响到视交叉(医院已经有了CT)!’后来我又亲自给这位病人复查了视野。”
当时的视野是一个进修的陈医生查的,该病例的确是垂体瘤,但病变还未影响到视交叉,也就是说陈大夫的视野图并不真实。艾老师后来去问过陈大夫,才知道他查视野时与病人的沟通方式不对。
有吗?有吧。
-有
有吗?有吧。
-有
没了吗?没有了吧。
-嗯
一定不要误导了病人,因为病人往往会因为医生说“没有了吧”他就会觉得没有了。
您眼睛盯住中间的白点不要动,看旁边这个小红点,如果看到有,就说‘有,有,有’,如果看不到了,就说‘没有,没有,没有’。
05“挖掘垂体瘤引起视野缺损的‘根’。”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垂体瘤的治疗手段还非常有限,主要的治疗手段是手术,放疗加以辅助。针对一些疑难病人,虽然可以通过视野检查推测出垂体瘤,但是X光、脑血管造影、气脑造影等原始的影像学手段只能提供大概的判据。神经外科的医生认为“不能凭一个小小的视标、视野图就开刀的!贸然手术风险大”,这种情况下,就非常需要多个科室的会诊和讨论。
年,为了能更有效的诊断和治疗垂体瘤,在协和内分泌科史轶蘩教授的倡导下,正式成立了垂体瘤协作组,开始对垂体疾病进行联合会诊和研究工作,内分泌科、神经外科、眼科、病理科、耳鼻喉科、放射科、放射治疗科、麻醉科、计算机室9个相关科室参与其中。
“那时候,除了眼科接诊的垂体瘤病人,有内分泌相关症状(比如,闭经、溢乳、尿崩、甲亢等)的病人也都会被送到眼科检查视野,如果检查结果显示为垂体瘤,通常会再转至神经外科进行一步的影像学检查,对于疑难的病例会再进行垂体瘤协作组的多学科讨论,最终确诊。”
据资料统计,从年到年,劳教授带领眼科共查垂体瘤病人视野近人次,观察垂体瘤对视功能的损伤,为垂体瘤协作组的研究项目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并且,通过分析上千例垂体瘤视交叉综合征,劳教授发现虽然临床资料表明有的肿瘤很小,但是视野损害却很明显,因此大胆地提出“视交叉与垂体分享同一血供”的假说。年开始,劳教授指导学生高桦、钟勇等进行了“视交叉的血供研究”,证实了自己提出的假说——垂体瘤“盗血"的重要特征,为垂体瘤引起的视野缺损找到了解剖学和病理学依据。
年,垂体瘤协作组最终的主要研究成果《激素内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及基础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项目进行的十几年间,垂体瘤协作组的大夫们兢兢业业、严谨求实,实现了多个国内垂体瘤领域的‘第一次’,有的成果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因此,垂体瘤项目的获奖是非常有必要的,实至名归,老一代协和人付出了血汗,这种团结、合作精神应该永远发扬光大下去。”
劳教授退休以后仍然经常来科里,给晚辈指导疑难病例的诊疗,后来生病以后,待在家里,还常跟艾老师说“姑奶奶,我还想来科里,来科里看看,跟你们聊聊天。”为了让劳教授安心修养,艾老师会经常给劳教授打电话,会去家里看她。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劳教授的一生为神经视野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今,随着视野机的进步,视野检查的过程由过去的人工变成了全机械化,检查的时间由过去的一小时左右缩短到了十几分钟。现在视野检查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眼科疾病的必查项目之一,仅医院眼科门诊每天就平均需为二十多位病人检查视野,帮助确诊相关疾病。
劳教授开创的神经视野学在发扬光大。“协和精神”要传承下去!
访谈后记
与艾老师医院眼科门诊的一个空闲诊室,我们早到几分钟,随后艾老师手捧一个长方形木盒进来。原木色,有两个合页,其中一个掉了一半,一看便知有些年头了,我顿时想起了小时候外婆收纳用的小“百宝箱”。
“視野視標”里面装的东西跟今天的采访有什么关系?我们心里想。
不需多问、不需说什么,“珍惜”两个字就写在艾老师的脸上。
艾老师打开木盒,小心摊放在桌子上,“以前我们查视野就是用这个小视标”。这个小木盒在我看来也许仅是个旧物,而它对于艾老师来说是一种情怀,薪火相传,师情难忘。
曾经,它承载了一代人对一个学科的期待、一代人的技艺和智慧、一代人对未知领域的不懈探索、一代人的无私奉献,同时肩负着相邻学科疾病对视野学的重托。
时间会流逝,人终将老去,唯有“木盒”不惧时光,唯有医者的精神代代相传。
采访:廖莉莉王仁芳AMEPublishingCompany
成文:王仁芳AMEPublishingCompany
推荐阅读:
悬壶济世内分泌仁心仁术陆召麟
张以文:协和妇科内分泌学科发展见证人
周觉初:遇见放疗,相守一生
金自孟:鞠躬尽瘁内分泌博闻多识随境缘
点击“阅读原文”了解AME出版社。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